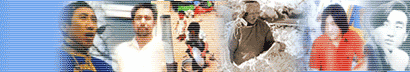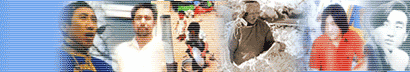< 返回目录 >
草原“出平湖”
中国青年报记者
江菲
“他们是弱势中的弱势,总得有人帮帮他们”
2003年6月,一个微弱的声音飘在互联网上。一个名为“曾经草原”的人在网络中到处张贴一封申诉信:“我的家乡东乌旗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优良的天然牧场……但是,我们旗委……这些年从各地招商引资兴办企业……在牧民们承包的草场上兴建造纸厂,没有污水净化设备,更不做环保评估,将工业废水直接向牧民承包的草原上排放……污水流遍周边草原,污染了18户牧民的承包草原1.5万亩,造成牲畜中毒、死亡、流产,直接经济损失二三十万元。牧民长年饮用被污染的水源,也出现头晕、恶心等症状。
“最后,旗主要领导竟把15年前明确划分给我们大队的草场(有蓝图为证,并已承包给牧民,共约1万亩)以‘当时划分有误’为理由收回……”
信的落款是:内蒙古、锡盟、东乌旗、乌里雅斯太镇、恩和吉日嘎朗嘎查(大队)、原党支部书记苏乙拉图。
这些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怎么会使用互联网呢?
我找到了这个网名为“曾经草原”的人,一个在草原上生活过13年的北京知青。这封申述就是他从蒙文翻译成汉文又贴上网的。
他叫陈继群,职业画家。
1967年,陈继群插队到内蒙古最北边的大草原上。这里叫东乌珠穆沁,意思是:长满葡萄的地方。
说起当年的草原,陈继群一个劲儿赞叹:你想吧,齐腿高的草,绿油油的,那么开阔的视野,那么清新的空气……
回北京后,陈继群每年都要回草原写生。每年回去,陈继群都发现草原有些变化:锡林浩特的沙子已经上房了;很多牧民养起了骆驼;沙化的草原面积越来越大;大片的草地被出租给农民“开荒”;草原上甚至开始出现了工厂、矿山、钻井机……
陈继群坐不住了。
2000年,在陈继群曾经插队的草原上,突然出现了几家工矿企业,引起了他的关注。它们不仅侵占了牧民承包的草场,还将生产过后的污水废物随便遗弃在草原上。牛羊成群地死去了,牧民的水井遭到了污染。
“草原的生态结构是非常脆弱的,怎么禁得起这么污染?”陈继群决心帮牧民“抗一抗”。然而他发现:牧民们根本不了解能够保护自己的法律。他和几个知青跑遍了北京、呼市的各大书店,一本蒙文版的法律书都没找到。
他们开始自已集资请专业人员将有关法律译成蒙文,再请出版社出版。曾在法律出版社工作过的程小路女士听说了这件事,找到他们,说自己非常内疚,因为这本应是出版社的工作。程小路捐了1500元钱,说“我帮不了什么忙,就出点钱吧”。就这样,第一本供牧民使用的法律合订本就这样面世了,包括《草原法》、《环境保护法》、《矿产资源法》和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。
书出版后,他们开车到牧区,无偿交到牧民手中。最初印的1000册,很快就发光了。
“让他们知道法律法规还只是第一步,要有人去帮他们普法。很多单词蒙文中没有,都是汉语音译过去,我们不是专业人员,也讲不明白,现在只能靠牧民们自己悟。”陈继群依然很忧虑。
“牧民们生活在偏远的草原上,交通通讯不便,又与内地语言不通。他们是弱势中的弱势,却守着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生态环境,总得有人帮帮他们啊。”
“我们不能接受这个决定,我们不能就这么妥协”
2003年7月,我来到内蒙古东乌旗实地调查。
牧民们领着我走,没多远,就闻到了空气中一股说不出的味道。我问是不是牛羊粪便的味道,他们使劲儿摇头:就是那个地方臭水的味道。
爬上一个高坝,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大片“湖水”,有人戏称其为“草原出平湖”,“东乌旗特有的风景”。牧民捡起一块石头,抛向“湖”中,“咚”的一声,卷起一股黑黄黑黄的水花,令人作呕。
牧民说,你看那边那个冒烟的地方,就是那个造纸厂排出的臭水,从2000年到现在,一天也没停过。我问这片污水池的面积,他们说了个令我咋舌的数字:“4000多亩”———这还是政府丈量得出的。
达木林扎布家,是被侵占牧场的7户牧民之一,就居住在离这片污水池500米左右的地方。他是1991年前的大队老支部书记,也是被占用草场7户牧民上访的带头人。
据他介绍,1984年,国家开始实行草场承包制。1986年,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口号和旗政府的领导下,这里开办了一家造纸厂。由于生产技术一直不过关,开开停停,1999年宣布破产。2000年,盟里招商引资,将厂房以每年50万元的租金、租期15年,租给一个从河北来的私营企业主,更名为东乌旗淀花浆板厂,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和污水排放。
老人清楚地记得,2000年3月,几辆推土机开了进来,在草场上垒起了坝。“没有跟我们打过任何招呼,没有协商,没有征用,凭什么这么破坏我们承包的草场?”
当年6月,达木林扎布和苏乙拉图联合受害牧民写了第一份抗议书,要求尽快恢复被侵占草场的所有权,恢复生态环境,并对牧民的损失予以赔偿。
“你们把这封抗议书送到哪里了?”我问。
“哪里都送了,镇里、旗里、盟里,自治区都去了两次。”
结果,当时的旗长训斥他们:造纸厂的事我不知道,你想告就告去!
在自治区,他们被从人大信访办推到农牧厅,又推到草原监理站。监理站的人对他们说:破坏草场我们能管,环境污染我们管不了,你们得去找环保局。环保局的人打电话问锡盟环保处,对方说:造纸厂确实有点污染,但这是厂方和盟公署、旗政府签的合同,他们管不了。这么跑了好几个月,不是说“过几天解决”,就是根本没人搭理。
“你们没找造纸厂理论吗?”我问。
“咋没找呢!”格日勒说,“造纸厂说,这地是政府给他们的,厂子也是租政府的,要找也得找政府呀!”
2000年10月25日,东乌旗政府下达了一份给牧民补偿的通知。通知中说:按每亩每年3元标准,对牧户进行为期15年的补偿(浆板厂的租赁期为15年)。“我们不能接受这个决定。”达木林说,“这个数字没有同我们协商过,也没有明确对草场污染问题的处理,我们不能就这么妥协。”
造纸厂开工不到一年,附近的牧户就发现自己的井水出了问题。
“煮奶茶,明明都出颜色了,盛出来,就分出两层:有颜色的凝固在下面,上面还是清水。”达木林说。达木林的三儿子还特意从井里打了一杯水回来给我看,静置不到5分钟,杯底就出现一层白色沉淀物,将水烧开,沉淀物更多了。
“我们家的井水都黄了,一看就不能喝了。”乌日图说。
从那时起,有条件的人家,都开着车到十几里地外的井里去打水,供人饮用,但牲畜仍只能喝原来的井水。
上访迟迟没有结果,污水一天天增多。终于,2001年12月14日,由于污水结冰膨胀,挤压堤坝,引发了大规模的溃坝。污水喷涌而出,所淹之处,迅速地蒙上了一层黑褐色,牧民们看着被污水围困的牛羊,不知所措。
牧民巴特尔说:那水,就像酱油似的,粘粘乎乎的,流到哪儿,就粘到哪儿。
牧民图门吉日格拉说:我们的网围栏有4尺多高,水淹得只剩一个小头儿。
牧民们找到旗政府,答复说:你们不是能告状吗,告状救牲畜吧!
据牧民们统计,这次溃坝共造成18户牧民约2000头(只)牲畜的损失,污染了草场2000多亩。而据东乌旗政府2002年3月发布的文件,这次溃坝污染的草场面积达到4293亩,相当于又建了另一个污水池。
溃坝的第二天,达木林又写了第二份上诉材料。
结果是,盟公署派工作组,到牧民家做了一个月的工作,告诉牧民:告状需要大量时间、金钱,又不一定能解决;应以大局为重,通过协商解决问题,造纸厂对旗里有很大贡献,不能停产。
格日勒说:“他们还跟我们讲,这水是没有毒害的,经过净化达标的,过不了多久,还能让我们喝!”她撇撇嘴,“我才不信咧。”
“我要问问他们,为什么造纸厂重要,我们牧民、牲畜都不重要?”
2001年溃坝的污水一直存留在草原上,直到第二年夏天才渐渐消失。
除了在溃坝中死亡了大量牲畜,污水的影响越发明显。靠近污水池的牧民们反映,他们牲畜近两年抓膘率下降,每只羊平均少产半斤至一斤肉;春季接羔率也从原来的100%下降到70%;绵羊开始大量掉毛,山羊产绒量下降。
污水池长年随风蔓延的恶臭,熏得大家头晕,恶心,晚上睡不着觉。
看到上访解决不了问题,牧民们在大队书记苏乙拉图的带领下,拿着自己的《草场承包使用证》,准备通过法律渠道,收回被侵占的牧场,关闭污染企业。
2002年8月7日,内蒙古锡盟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,并根据租赁合同,将东乌旗政府列为第三人。
在离污水池几十里地外,我们找到了苏乙拉图。
法院立案后,苏乙拉图一天也没闲着。
他说,从2002年11月起,镇党委、旗党委就隔三差五地找他谈话,告诫他:“你不要老领着牧民打官司,把牧民变成贫困户。”还说,“应该尽量协商调节,不要闹到法院去。”
不久,盟里又派下来工作组,要求苏乙拉图一同到牧民家做工作,把污水池占用的牧场“收归回去”。苏乙拉图说:“和牧民签了30年的承包合同,怎么能说收回去就收回去?”他要求开个群众会议,投票表决,如果大家都同意收回去,他就同意。
工作组说他“不服从组织”。
2002年12月14日,苏乙拉图被通知到镇党委开会。他一到,就听到宣布决定:罢免苏乙拉图的大队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职务,没有给他任何理由和解释。“我对职务没有任何兴趣。”他说得十分沉重:“但是,地上被污染了,地下被挖空了,将来子孙们还怎么生存?!”
在工作组的“工作”下,起诉的7户牧民有4户撤诉了。
乌日图、巴特尔、图门吉日格拉说,旗政府一天找他们两三次,两三天到家里来一次,动员他们撤诉,还要收回污水池占用的牧场。
乌日图说:“他们当时跟我们说,快撤诉吧,其他人都撤诉了,就剩你一个人,怎么能打赢呢?”其余几户纷纷点头:也是这么和我们说的,还许诺了很多优惠条件,我们就撤诉了。
乌日图的妻子莲花在一旁比比划划大声说:“他们的条件是骗局!我根本不同意撤诉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?”我问。“我要求他们,把答应的条件都写下来,盖上章,他们不干,还不是骗局?”
坚持继续打官司的其实就是达木林一家,另外那两户,一个是他大儿子芒来,一个是他弟弟巴特尔。
达木林对工作组的回答是:“盟委的决定,对的,我听;错的,我坚决不听。”
2002年末,东乌旗乌里雅苏台镇人大会议期间,66名人大代表中的33人联名提案,要求依法停办东乌旗淀花桨板厂。
然而石沉大海。与会人员称,提案根本没在大会上宣读,事后也没有任何有关部门给予答复。
乌镇镇委书记鄂尔登陶克陶在接受采访时坦然地说:
“苏乙拉图不领着牧民发家致富,反倒领着几户牧民到处上访,还大搞个人主义,不把镇、旗政府的决定放在眼里,是不合格的支部书记。
“至于人大提案,那不是我们镇政府能够答复的。我们已经向上级机关汇报过了。”
2003年3月,污水池再次发生溃堤,乌日图家淹死了67只羊。“大水一冲,羊都吓坏了,反倒跑到水里去,眼睁睁地看着淹死了。”莲花几乎哭出来。
“国家要用,收回来不行啊?你们北京要修路架桥,让老百姓搬还能不搬?”
东乌旗政府主管工业和交通的副旗长刘阿军接受了采访。据他介绍,这家工厂去年产值已达8600万元,上缴利税200多万元,算上带动的其他产业,给旗创造的利税有400多万元,相当于全旗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。
对于造纸厂存在的问题,他说,“造纸么,我们原来真的不了解。谁想到天天用的纸还有污染啊!”
“难道浆板厂的老板没提醒你们?”“这种事你不提谁说呀?”他回答。
但是,在2000年河北安新寨里造纸厂承租合同的附件里,东乌旗政府作出了这样的承诺:
为承租方办理各项相关手续给予大力协助(如“排污许可”、工商登记、注册、税务登记等);同意承租方按照国家产业政策,以“污水黑白液分流、氧化塘处理”的方式,对造纸污水进行治理,并向承租方“无偿划拨足够排污及治理的场地”……
而据浆板厂厂长孙国庆讲,当时是镇党委书记骑着摩托领着他来划地,“不然我也不会来的”。
至于污水池占地问题,刘旗长和孙国庆都说:那儿原来就是碱水泡子,根本不长草。锡盟造纸集团是国有企业,土地理应也变成国有。但是,1997年第二轮承包时,企业正在破产,就承包给牧民了。
“这是个错误,我们将牧场收回,只是为了纠正错误。”他说。
我要求看看整个旗里的土地划分示意图。刘旗长表示,直到现在,也没有一个详细的牧场归属图可供参考。
当地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极不耐烦地说:“你理这干啥?这地都是国家的,又不是个人的,国家要用,收回来不行啊?你们北京要修路架桥,让老百姓搬还能不搬?”
我提醒他:城镇用地和牧民承包的草场是两回事,何况牧民手里还有承包证书。
他说:“承包给你的就是你的了?不还是国家的?”
2003年1月,东乌旗政府以1997年第二次承包草场划分错误为由,将淀花浆板厂厂房及附近的10730亩牧场,化整为零,同时签发了5份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,正式“收归国有”,租赁给淀花浆板厂使用。在这些证书中,除了有牧场的面积外,没有四至界线,没有地号,没有图号。
根据1988年通过的《土地管理法》(修正)规定:一个建设项目需要使用的土地,应当根据总体设计一次申请批准,不得化整为零。分期建设的项目,应当分期征地,不得先征待用;国家建设征用耕地一千亩以上,其他土地二千亩以上,应由国务院批准。
2003年3月,锡盟行署向国家环保局提交了一份报告,其中清楚地说明:“关于造纸厂及排污池占地,至今未能找到证明其四至界线和权属面积的文件”。
这份报告还提到:“1986年成立的造纸厂,设计产量为年产1000吨”。而据刘旗长和孙厂长的介绍,现在的东乌旗浆板厂,设计产量为年产5万吨,已经达到年产两万吨的生产能力。一个年产1000吨工厂的排污量和所占面积,怎么能和一个年产两万吨工厂的排污量和面积相当呢?
如果污水池本来就在造纸厂占地范围内,为什么旗政府还要承诺“无偿划拨”?为什么在村民最初反映问题时,政府没有发现承包时划分牧场有“错误”,还下发了一份承认污水池占用牧场的文件?为什么在事隔1年后,当牧民们诉诸法律解决时,政府才“恍然大悟”发现了错误,急忙“纠正”征回?为什么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上,没有地号图号和四至?
牧民们给了一个最直接的回答:不知道谁在瞎说!谁能想像全国公认最好的一片草场,能有几千亩不长草的荒地?
内蒙古大学环境与生态科学院的刘钟龄教授在2001年就听说了这家造纸厂,并到当地了解过具体情况。他坚定地说:“那里原来肯定不是荒地。我去时,污水还不深,从水面上还能看到许多露出的芨芨草。我判断那里原来是芨芨草滩,是冬天放牧不可缺少的避风地。”
“早知道交这么多排污费,我在河北还不是一样开厂?”
说到污染问题,刘旗长和孙厂长显然自信多了。
2002年,浆板厂安装了中段废水处理设备,并于9月通过了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的监测。
我问孙国庆:什么是中段废水?
这位自称从1987年开始办造纸厂的企业主答:就是蒸煮出来的水啊!
“那造纸过程中,除了中段废水,还有哪些废水?”
答:“那就是生活废水了。”
但是,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站曹立平处长的回答是:中段废水是指造纸过程中的纸机废水,我们通常叫“白液”;除此之外,最重要的废水是蒸煮出来的废水,也就是“黑液”,这也是污染最严重的工业废水。
而孙厂长对纸机废水的说法是:那是干净的,根本不需要净化处理。
曹处长说,即使是合格排放的废水,也并非没有害处,应该存放在防渗漏的地方,防止对地下水造成污染。
2002年6月,他接到牧民举报,曾亲自到东乌旗浆板厂实地考察。他说,即使有新建的防渗漏污水池,原来污水池里的水也根本没有补救办法,浅层地下水肯定已受到污染。
孙厂长和刘旗长都说:伴随污水处理设备上马新建的水塘是防渗的。他们还强调,这个地区地下四五米深就是粘土,这种地质本身就是防渗的。
“啥防漏,就是拿点编织袋子,装满土堆上。”始终观察造纸厂一举一动的牧民们说。东乌旗环保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对我说,从没有对造纸厂污水池所在地做过详细地质分析,也没有证据表明红粘土就能防渗;就算是能防渗,也不能防止污水在粘土层以上横向扩散,污染更大面积的浅层地表水。
我向负责污水设备监测的内蒙环境监测中心站询问,得到的回答是:我们只负责废水处理设施的监测,没专门对水塘进行监测。锡盟环保局回答是:惟一一个懂技术的人外出学习,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,没有办法回答。
我问孙国庆:你们的黑液排放能占总排污量的多少?
他自信地回答:10%,有时候更少,8%。
旗环保局的人士对此嗤之以鼻:没有安装任何流量控制测量装置,他凭什么说是10%?北方交通大学环境工程系教师尹承龙在2002年6月对造纸厂进行了实地调查:“这里面的数据太惊心了!污水里的酚、汞含量都严重超标。”他一直摇头:“最关键的是,这些污水没有去处,只能堆放在地表。即使是合格排放,是防渗水池,年复一年的生产应该修多大的污水池才够用呢?还不是要继续侵占牧民的草场?”
他更肯定地说:“何况,从专业角度判断,以这家造纸厂的规模,如果要对污水完全处理,那就几乎无利可图了。”
旗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还透露,按照该厂的排污量,他们预计应该缴纳排污费64.8万元。然而当他们下达缴费通知单时,厂方却十分不满地说:“早知道交这么多排污费,我在河北还不是一样开厂?”最后,由旗政府出面做工作,浆板厂只交了两万元的排污费,还总是拖延。“就是这点钱,后来也被变相地还给造纸厂了。”
从东乌旗水利监察大队,我得到了大致相同的信息:由于没有水表,据水利局估算,浆板厂每年使用深层地下水约200万至300万吨,但在旗政府的交待下,每年只交纳1万元的水资源使用费,最多一年,也只交了1.5万元。
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对此十分担忧:“除去闻得到的空气污染之外,会不会导致深层不可再生地下水的枯竭,我没有把握。”他说曾向旗领导反映,旗领导总是回答“够用”,但没有一份对地下水资源总量的勘测报告,他始终放不下心。“用这么点经济利润造成这么严重的环境问题,我认为是得不偿失的。”
我问孙国庆:从河北到这里来发展,那原来的厂子怎么办?
他回答:有家里人在看着呢!
但是,我从河北省安新县政府得到的答复是:寨里造纸厂超标排污,于1999年底被安新县政府依法关停。
安新县寨里造纸厂与内蒙锡盟及东乌旗签订租赁合同的日期是:2000年1月12日。
“什么也不能发展,就当好北京的‘绿大门’,那我们吃什么喝什么?”
采访中,我问刘副旗长:你知道牧民打官司的目的是什么吗?
他说:就是想让造纸厂关门。我问:那你赞同吗?他迅速地回答:“当然不赞同。”
他说,没有任何一个地区能够靠单一的经济模式获得发展,牧区也不例外。“世界上哪个发达国家不是依靠工业取得经济腾飞的呢?”
从2000年起,因连年自然灾害,国家决定免收牧民的牧业税。
“如果牧民纳税,我们本来能有5000多万元的收入,这一免,就跌到底了。”“全旗这么多职工等着发工资,国家要求修公路要补贴,教育部要求实现某某规划要花钱,没有税收,钱从哪儿来?”
他说,“你也帮我们呼吁呼吁,给我们加加工资,我每月只拿1300多块钱,什么规定的补贴都没有———没钱啊!”
“环保团体的观点就是:你们什么也不能发展,就得当好北京的‘绿大门’,”他有些激动,“那我们吃什么喝什么?”
“达木林想让造纸厂关门,哼!我今天话就这么说,让他一家受了损失,我扶贫也扶得过来;让这么多人吃不上饭,我们靠什么救啊!”
但是,造纸厂真的为东乌旗的财政做出了巨大贡献吗?在《东乌旗人民政府承诺函》中,有这样几条:“除每个租赁年度收取5万元的水资源费、两万元的排污费,在租赁经营的第6年度起以规定的标准收取厂内的土地使用费外,不向承租企业收取摊派任何费用”;
“保证对承租方在经营期前7年缴纳的所得税全额实行即征即返。增值税地方留成的部分,7年内向承租方即征即返50%”。
承诺函的备注中称:“如旗人民政府违反该承诺,承租方有权单方解除出租方的租赁合同,并由出租方返还投资,赔偿损失”。
如此“优惠”,近于免税,淀花桨板厂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到底有多少,除了旗政府,恐怕谁也说不清。草原经济的发展真的非需要这样的工业不可吗?
农业部畜牧兽医局局长贾幼陵说:在牧区发展工业要依法进行,从建厂前的环境评估,到生产后的生态恢复,该履行的手续一个不能少。
“但是,我们希望尽量不要占用草原。对占用草原的,除了要依法办理征用手续外,还应该交纳高额的草原补偿费,由政府负责对牧民进行补偿,对草原进行回填,尽可能恢复草原植被和生态。”“那么草原补偿金的征收方法和标准是什么?”我问。
“这个,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。”
“可是,一些已经办起来的对环境有污染的企业该怎么办呢?”我问。
“那当然也要依法治理。”
“但比如东乌旗桨板厂,牧民上访、环保局介入也已经快两年了,为什么还在继续?”
贾局长说:“这当然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。”他认为,说牧业税减免影响了地方的财政收入是无稽之谈。据他了解,国家减免牧业税后,对地方政府给予了大量的财政补贴。
“这和地方的政府体制也有很大关系。东乌旗只有5万多人口,却是党政人大政协四套班子俱全,这么少的人口养活这么多的公务员,确实负担很重。”
“我个人认为,在草原上发展造纸工业是极不合适的。”贾局长说,“草原上的造纸原料就是芦苇,或者柳条,而它们都是重要的保水植物,对草原生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是不能够随便砍伐使用的。”
国家环保总局的曹处长告诉我:如果到西部多走走,会发现这样的企业特别多,管都管不过来。“有的时候我就想,国家真的缺那么几千吨矿、几万吨纸吗?”他摇头,“我看不缺。可我们缺那样的草原。”
今年4月,修改后的《草原法》正式生效。农业部新成立了草原监理中心。中心主任宗锦耀认为:“政府应该是市场规则的制订者、企业行为的监督者、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环保工作的执行者。但从事情的经过看,东乌旗政府似乎是为企业说话的,这可非常耐人寻味呀!”
据他介绍,我国共有60亿亩草原(草地),内蒙古自治区就有11.8亿亩。“但是,内蒙古地区90%以上的草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沙化、退化、盐碱化现象。”
我问:“有人说,东乌旗草原是我国最好的天然牧场和保存最好的草甸草原,是吗?”
两位农业部的官员都毫不犹豫地点头说:“是!”
但是,为保护这片最好的草原,在法庭的一边,只是一户牧民;另一边,是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税收的污染企业和大力支持企业的旗政府,双方强弱之势不成比例,法律将站在哪一方呢?
< 返回目录 >